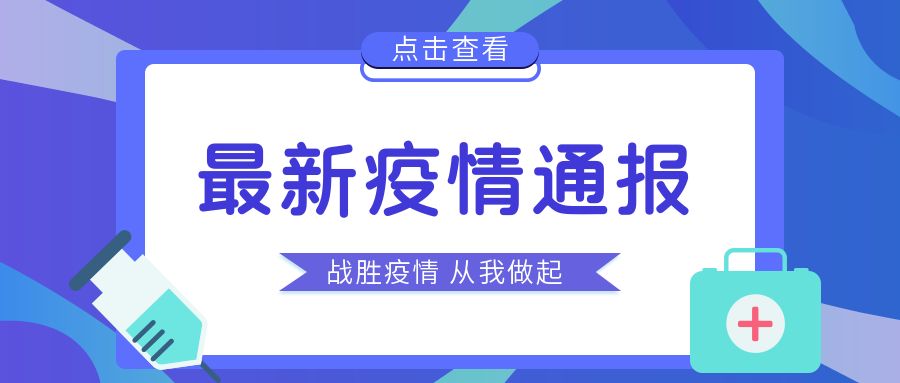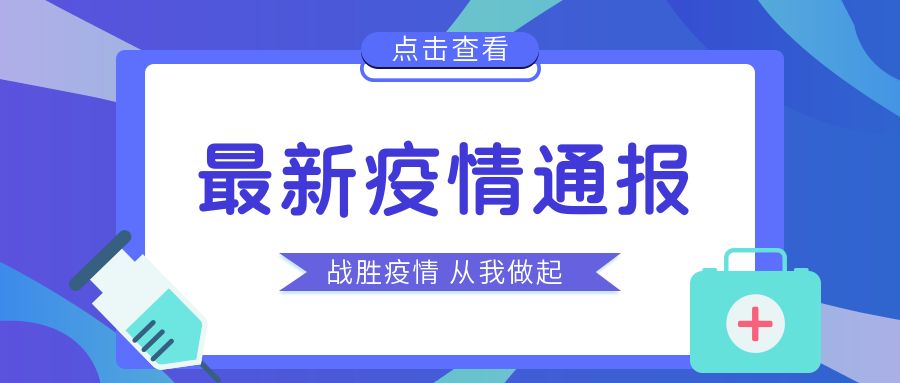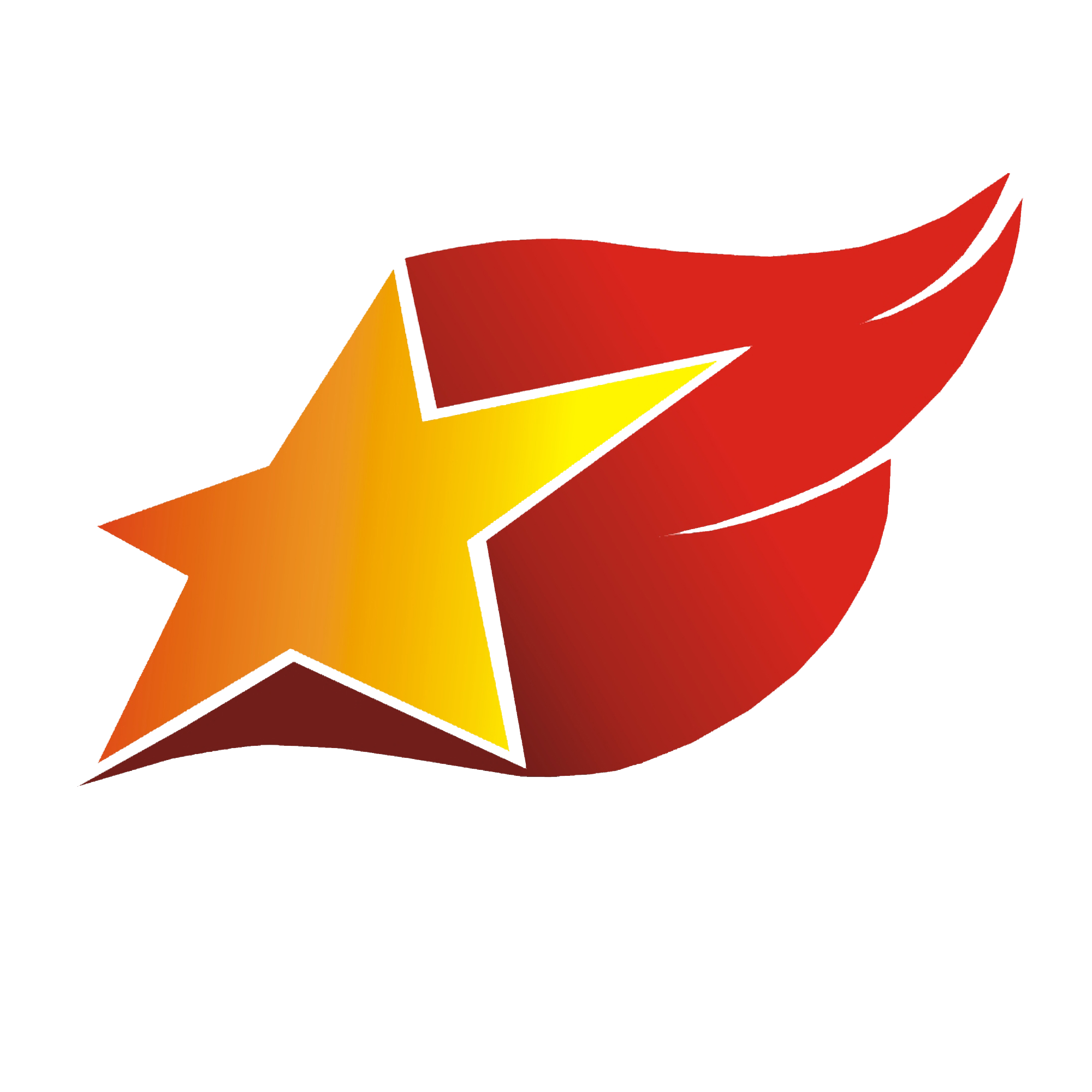颜仲康
1962年,印度在国际反华势力支持下,扩张领土的野心恶性膨胀,不断地在地处喀喇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的中印边界西段的中国境内(新疆奇普恰普河谷、加勒万河谷以及西藏阿里地区)进行军事入侵和挑衅活动,并公然在我领土上不断建筑军事据点,进一步蚕食我国领土,蓄意坚持使用武力,使中印边界武装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我国政府对印度政府的侵略扩张行径多次提出照会、抗议和警告,但是印度侵略军却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地连续挑起更严重的事端,竟然向我边防哨所发动进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驻中印边界西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边防部队坚决执行中央命令,为了保卫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坚决收回被印度侵略军占去的领土而奋起反击。于是,一场震惊世界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打响了。
我军与印度侵略军由短兵对垒到我军大举反攻,前后历时4个多月。最后,这场战争以印度侵略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为了中印边界作战运输的需要,新疆军区除动用现役运输部队外,还命令坚持屯垦戍边、建设边疆的生产部队—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从生产运输单位中迅速组织人员车辆,奔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前线从事战地支前运输服务。为此,兵团党委于1962年7月24日,给独汽三营(现三运司)下达了组织运输连队支援前线作战的命令。
独汽三营层层进行简捷有力的支前政治动员,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组织支前党支部,配齐强有力的党政领导,明确了支前任务、权限和责任。对车辆的技术状况、修理保证、配件保证等都做了周密的安排。1962年8月1日,由100多人和78辆汽车组成的支前汽车连准时出发。在连长张林孝的率领下,车辆统一编号,依次去南疆军区某部,装满前线所需的作战物资和生活物资之后,随即向叶城的后方基地进发。在叶城后方基地,支前汽车连除向基地首长报到,接受新的运输任务,统一换上没有帽徽、领章的军装外,还向有关方面了解新藏公路的路况和高山反应的病症与解救方法。未来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客观的自然环境也的确残酷恶劣。独汽三营支前人员虽然驾车已无数次纵横天山南北、长城内外,也曾多次攀高越险,圆满地完成了各种运输任务,但从未驾车跨越这巍巍昆仑之路。面对眼前这繁重的任务和实际困难,他们没有畏难气馁,决心要在未来的战地服务中一显自己不凡的身手。
支前汽车连按照高原行车特点对全连人、车作了新的安排,在连长张林孝等分头带领下,分作三批离开叶城后方基地,开始向藏北高原阿里方向奋勇攀登。途中,高山反应随地势升高逐渐作用于不适应的人们。沿途路面之差、路段之险、气候之恶劣,也是他们前所未见的。他们终于将第一次从喀什装载的军用物资,按后方基地的要求,安全准时地运至前线指挥部驻地康西瓦。此后,他们开始在中印边界前线的战地支前服务,多次执行前线指挥部命令,将部队作战人员和弹药物资,按照具体要求分别送到中印边界我方前哨阵地。这些前哨阵地大都在海拔4000—6000多米高度的高原山岗上,行车往来其间,不但道路险峻难行、高山反应强烈,而且在中印双方犬牙交错的路段上,常有印军的封锁和印军飞机对我战地车辆的袭击。
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正式拉开序幕后,支前人员前后有几批执行前指紧急命令,返回喀什和叶城,昼夜不停地向前沿阵地运送作战部队和军用物资。
1962年10月9日,前线战斗正酣时,汽车连执行前指命令,迅即下山从喀什运送23辆车的作战部队、弹药到海拔6000多米的天文点阵地。他们不怕疲劳,持续行车四天四夜,走完了1300多公里的艰难路程,完成了任务。
1962年10月21日,张林孝奉命急率18辆车返回叶城基地,火速运送炮弹、汽油到康西瓦。他们如离弦之箭,争分夺秒,一天一夜没睡觉,连续行车完成了第二次紧急任务。
在每一次高原战地服务中,无论去哨所阵地车辆有多少,支前汽车连都事先指令一名干部或确定的负责人率队前进,做到队队有干部、车车有负责人,保证集体互动,人车安全。在每一次行车中,为了战斗的需要,为了抵抗疲劳与瞌睡的困扰,驾驶员们用吃冰、吃雪、脱掉帽子把头靠在车门窗上让冷风劲吹的办法,保证车辆随时可以开动,每天的出车率达75%以上。这在参战的汽车运输单位中是最高的。
上山以来缺氧引起的头晕、恶心、呕吐、流鼻血、周身发软等反应已成了家常便饭,高山上的寒冷是更不用说。为了战争的胜利,给祖国人民争光,给并肩作战的边防军人和自己争气,他们默默地忍受肉体上的痛苦。许多驾驶员曾经多次冒着生命的危险,在雪域高原驾车往来奔走,留下了一幕幕动人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有的驾驶员把车开到目的地时,由于高山反应持续加重,已没有力气去打开车门,体力到了衰竭的地步,常常是目的地的战士去打开车门,并把他们扶出驾驶室;有的驾驶员到达目的地,虽然能咬紧牙关把车门打开,但由于体力不济,却随车门的打开而一头栽倒在地;有的驾驶员下车后即发生呕吐,但吐的却是吓人的黑水—浓浓的胃液;有的驾驶员由于是带着高山反应坚持行车,用意志在与低氧环境搏斗,就在人下车之后的瞬间,随即进入眩晕的昏迷状态……
这些场景,让在场的每一个人不止一次地流下了泪水。
从我军反攻开始到战争胜利结束,在张林孝率领下,汽车连始终配合部队行动。其中,有29辆汽车和人员直接配属前线部队。其余为参战部队后勤、战地医院等单位运送作战部队和作战物资,护送前线伤员和战利品,有时也向俘虏营运送印军俘虏。在激战的天文点各个阵地,他们一个个义无反顾,为了胜利,为了减少我军的伤亡,争分夺秒地做好战地服务。他们都接受了血与火、生与死、高山反应、恶劣气候、道路险峻难行的重重考验,充分展现了兵团一代人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精神风采。
在前线,从后勤基地去我军前沿的不少阵地,有的路段与印军据点相距很近,常有印军火力封锁我车辆通过。为了完成向前沿阵地运送兵员、弹药和投入战备车辆的任务,他们大都是在夜间冒着生命危险,闭灯行驶。在去西藏阿里地区班公湖的边防前哨阵地,有一段长达30—40公里的路段在印军火力封锁区域内。这里坡徒山险,湖山相依,稍有不慎汽车就会有掉入湖、掉入坑、坠崖或碰山的危险。他们总是沉着机智地驾驶着汽车,勇敢地冲过敌人的一处处火力封锁,安全到达前沿阵地。
在炮兵团一营二连的驾驶员刘增新和助手李石海按炮兵团长命令,提前四天就把火炮和炮弹拉运到海拔6400米的11号炮兵阵地。那里无水、无饭,天气特别寒冷,他们所穿的旧棉军衣很难抵御这高山奇冷。他们凭借坚强的意志,吃冰饮雪,车子保持正常状态,坚持在阵地上四天三夜,直到胜利,才拉着大炮转移。
在炮兵团一营三连的冯朝轩、李书庭、王志新、张运奎等同志,不但完成拉运大炮和弹药的任务,还在海拔5000—6000米的阵地上(空手走路还觉吃力)把一车炮弹,从车上背到炮位跟前,帮助炮兵配装炮弹上的药包。由于气温实在太低,手一拿上炮弹就被粘住了,往往被撕下一块流血的皮肉。由于他们出色的战地表现,炮兵一营三连党支部为他们请功。同时,为炮兵团服务的9辆支前汽车的人员也荣立集体三等功。
王志新个人技术过硬,不但精心管好支前的战地车辆,而且还管好部队的车辆,做到了每辆车能及时开动,对完成战斗任务起了重要作用。
在天文点的6号炮兵阵地上,驾驶员李兴义刚运来的一车炮弹在激战中已余下不多了,后继的运弹汽车尚未上来。这时印军飞机正在头顶上轰炸,枪弹从天而下,地面印军的大炮正在向我阵地逞威。炮三连连长再令李兴义立即驾车拉运炮弹。当李兴义顶着敌人飞机的射击把炮弹运到阵地时,大炮跟前只剩下3发炮弹了,他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完成了抢运炮弹的任务。
在工兵营的驾驶员艾光顺、马万英、李源泉则从喀什拉运作战物资,四天四夜连续行车赶到天文点前沿阵地。将近100个小时的疲劳行车,可以说疲劳得让人看了都心痛。当时为了打开道路,让我军顺利进攻,追击敌人,工兵营必须完成地面扫雷任务。任务就是无声的命令,他们三人以大无畏的姿态,接受了运送工兵的任务,使工兵完成了扫雷任务。
共产党员周景山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志愿军老战士。自从支前上山后,一直在执行前线运输任务,完成任务一直很好。
有一次,他开车在班公湖附近配合我军阻击敌人,经过两天两夜连续作战将敌人打败后,上级命令该部暂时在原地山脚下休息待命。该部领导却要求周景山将车开往远离前线的后方去。周景山凭直觉觉得其中有问题,便利用间隙时间,将自己的想法两次逐级反映,最后由徐国贤副司令员命令该部原地待命,不得后撤。原来该部领导人听错了命令,因而才有后撤的决定。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周景山同志有着与众不同的政治责任感,他想的是怎样有利于我军战斗的胜利,而不是对错误的决定也去执行它。
年轻的共青团员胡友廷是一级修理机工,支前上山后,一直担任排除发动机故障的工作。他在前线的几个月中,一直是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
胡友廷不但是支前车辆的“健康保护神”,而且是许多驾驶员都值得信任、办事可靠放心的小兄弟。他很勤劳,乐于助人,经常帮助驾驶员加油、加水、发动车子。在雪域高原,支前驾驶员中流行一种说法:“如果有小胡在我的车子上坐着,我就不怕了。”一次,在海拔6000多米的天文点,空气稀薄,氧气不足,不仅人难适应,就是汽车也难以顺利发动,每次发动汽车都要摇车,这是最消耗体力的劳动。胡友廷总是喘着大口大口的粗气,强忍着头痛欲裂浑身乏力,坚持帮助驾驶员把车发动起来。当车子发动以后,他又带着疲劳随驾驶员出发了。
时年42岁的张林孝处处带头、以身作则,不怕疲劳、战胜困难,他带领汽车连圆满完成了支前任务。
张林孝率领着一批车辆第一次到天文点去。当时,天文点风雪弥漫,路面太滑,且是陡坡,车子不能开到哨所。为了坚决完成任务,他想出办法克服汽车前进挡不能上陡坡的困难—利用倒档,把一车车物资直接送入哨所。
1962年10月21日这一天,张林孝已从前线执行任务回叶城基地。叶城基地首长又命令他的18辆车拉运物资到康西瓦的前线指挥部,要求全长452公里的上山路程,必须一天一夜内赶到。当时他接受命令并动员车组驾驶员讨论,提出行车的办法,终于按时赶到了康西瓦。此时,康西瓦前线指挥部为了抓紧时间调动部队,将驻加勒万河的部队转移到日地宗的任务交给了张林孝车组。他坚决执行前指命令,急率车组去加勒万河。从康西瓦到加勒万河,有500多公里蜿蜒崎岖的山路,还要翻越海拔5000—6000多米的大红柳滩、奇台达坂、甜水海、界山达坂等危险路段,然后才能从界山达坂附近折向加勒万河。从加勒万河,从巨路返回界山大坂转向藏北的日土宗又是600多公里,这又是一条难行的路。部队早送到一天,就意味着战斗的胜利保证越大。一路上他们吃雪、啃冰块。从康西瓦到加勒万河拉运部队去阿里的日土宗,全程1100多公里,张林孝与驾驶员在10月下旬的风雪高原上,连续行车四天三夜,安全地把部队送到了日土宗,出色地完成了艰巨的任务,展示了兵团人不怕困难、顽强奋战的雄风。
在中印边界的新疆线段,我军彻底痛击了印度侵略军之后,紧接着在南面的西藏阿里迅速燃起了严惩印度侵略军的战火,战况异常残酷激烈。在天文点配合部队作战之后,随即奉命张林孝组织15辆车的车组向藏北的扎西岗边前线转移。这15辆车装载的全是作战物资。从天文点到扎西岗前哨阵地全程将近600余公里。15辆车从天文点出发,在赶到狮泉河边时,狮泉河这条其貌不扬的河给他们一道难题—河上没有桥梁,车上的物资要全部卸下来,再用羊皮筏子一筏一筏地分载过河。河水虽然不深,汽车可以勉强涉水通过,但河床上乱石及大坑小坑横布在汽车必经之处,必须用人力在河床上“筑”成一条汽车通道。30多人作了分工:先是集中卸车,把一车车物资卸于北岸,然后分组利用羊皮筏子往返装运物资渡河,最后集中全力,人工搬运河岸边的大小乱石,把汽车必经之路水下河床上的大坑小坑全部填平,将突出河床的乱石推走,使水下河床有一定的高度,成为汽车可走的通道。过河的行动,在冷冻的河边足足持续了一天多时间,全是在饥肠辘辘下作业的。当人、车、物资齐集狮泉河南岸后,他们怀着急切支前的心情,向战火纷飞的前沿阵地兼程前进。
1962年11月底,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全线结束,我军取得了彻底打败印度侵略军的全面胜利,打出了我们的国威和军威。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停战不久,根据中印外交谈判达成的中方向印方遣送印军战俘的决定,支前汽车连奉命执行运送印军被俘人员去扎西岗边防前沿交接地的任务。
1962年12月10日,是个很有纪念意义的日子。独汽三营这支100多人的支前队伍,经过132天的战争服务,经受了战斗的洗礼,战胜了一切艰难险阻,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下达的支前任务。这一天,他们迎着刺骨的寒风,迎着如浪的群山,向手足情深的边防官兵告别,然后踏上归途。
战后,新疆军区为支前的单位、人员评功。
新疆军区决定授予独汽三营汽车四连集体三等功荣誉,授予驾驶员王志新、傅洪章、李兴义、刘增新、冯朝轩、马万英、艾兴吉、肖全英、李源泉,副驾驶员李书庭、唐教全、张运奎、高经根,保养员李石海、赵顺经等15人集体三等功;授予汽车四连连长张林孝同志个人三等功荣誉,授予驾驶班长张志忠个人支前模范称号。
1963年国庆来临,新疆军区确定刘增新、张林孝二人参加新疆军区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英雄观礼团,于1963年国庆在北京天安门参加观礼。观礼团人员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同年,张林孝、刘增新二人出席了新疆第四届积极分子大会。
他们是多么可钦、可敬、可爱、可歌的人啊!
几十年前,他们用壮丽的青春、满腔的热血、惊人的勇气、顽强的斗志,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的服务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虽然他们从未讲述这段支前的经历,但历史始终记着过去有功于国家的人们。(作者系三运司退休干部)
来源:叶尔羌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