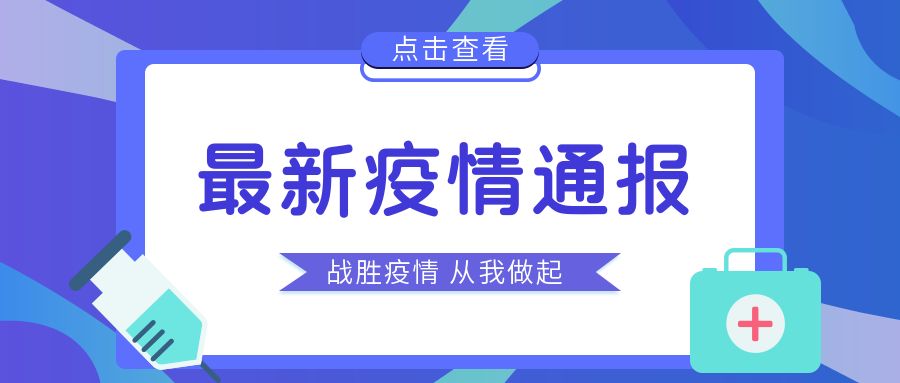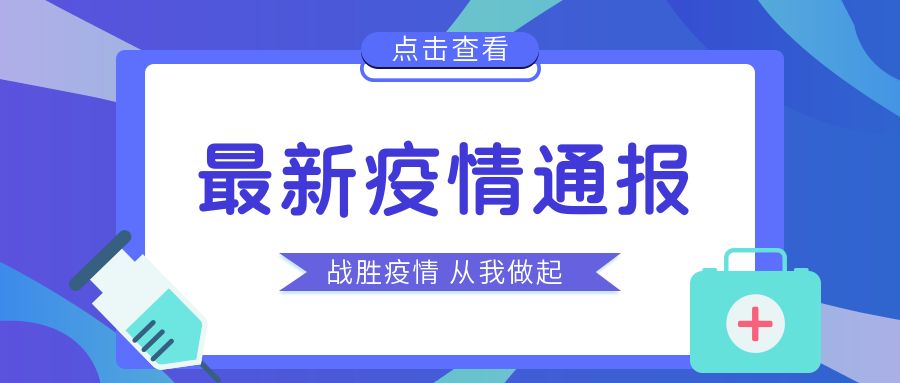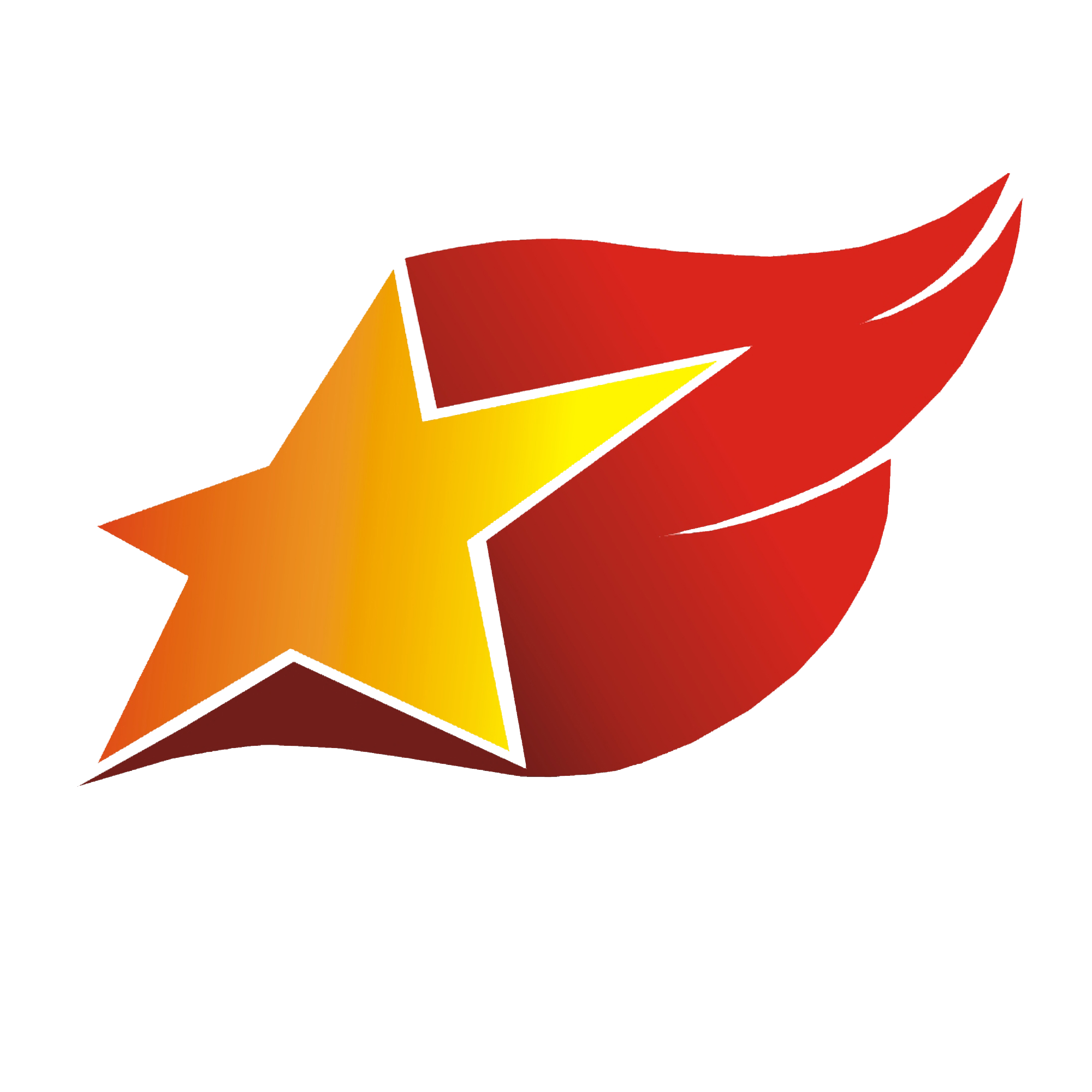●乔正明
1966年年初,我们在叶尔羌河畔新建的前进八场(现三师四十五团)一连开荒造田。7月,连里成立两个浇水班,为新开垦的近千亩地放水压盐碱,准备秋天播种冬麦。我被编在浇水一班,班长是老杨。
我们分白班和夜班,每天下午6时交接班,白班夜班10天一轮换。那时,上夜班没有其他补贴,唯一补贴是免费的一顿夜餐。每天晚上12时左右,炊事班小刘便挑着两只铁皮水桶来到农渠边,一只水桶里装着苞谷面馍馍,另一只水桶里装着菜汤。我们每人可以分到1个200克左右的苞谷面馍馍和两勺菜汤。那时粮食是定量供应的,而且九成是苞谷面。菜汤里的菜也不是新鲜的蔬菜,而是年初农八师无偿为我们支援的腌白菜。
虽然饭菜不好,但在那个年代我们都很珍惜,不会有一点浪费。现在回想起来,班长老杨还曾使一桶泥浆馍馍“浴火重生”哩。
记得一天晚上,炊事班小刘挑着担子来到农渠边上。按老规矩,我们把各自正在浇水的地块进水口堵小,让水流慢些,拿上搪瓷缸子去打饭。但走到跟前,我们都愣住了。只见小刘满身泥浆,他沮丧地告诉我们,刚才他正走在条田边的田埂上时,田埂突然塌陷,他掉进田埂旁齐腰深的一个水坑里。扁担一头的菜汤桶墩在还没有坍塌的田埂上,竟没洒掉,而另一头的馍馍桶却滚入水坑,几十个苞谷面馍馍都被扣了进去。苞谷面馍馍被他捞起时,全都被糊上了泥浆,成了灰不溜秋的泥浆疙瘩。
“我想再回去重新给你们拿,但那么多馍馍倒掉,我实在舍不得。杨班长,你看看这些苞谷馍馍还有没有救啊?”小刘说道。
这时,老杨蹲在桶边,从里面拿起一个泥馍馍,在马灯灯光下仔细看,自言自语地说:“是啊,这么一桶馍馍都倒掉,多造孽!”
有人说:“能不能洗一洗?”
老杨说:“可不能洗!馍馍已经泡酥了,如果再洗,泥浆没洗掉,馍馍就散没了。小刘,别着急,这桶馍馍烤一烤,完全能吃。地里的沙多,这馍馍烤干了,沙子也掉了。走,我和你去捡些柴火来!”老杨朝我们挥挥手,“你们先干活去,一小时内来吃饭!”
不一会儿,农渠边燃起一堆大火。大火熄灭半个多小时后,只听见杨班长喊:“吃饭!”我们到那儿,看到杨班长正用两根红柳枝拨拉开灰烬,又从里面夹出一个个黑疙瘩递给每个人,灰烬旁是大半桶热气腾腾的菜汤,小刘拿着汤勺给每个人的搪瓷缸子里舀汤。
拍打掉灰烬,那黑苞谷面疙瘩露出焦黄的皮,散发出一股夹杂着土腥味的特殊香味,同时还有点硌牙的感觉。大家啃着烤苞谷面馍馍,喝着热菜汤,时而逗逗小刘,时而夸夸老杨,嘻嘻哈哈地吃得津津有味。一桶泥浆馍馍“浴火重生”,一点也没有浪费,大家都格外高兴。
来源:兵团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