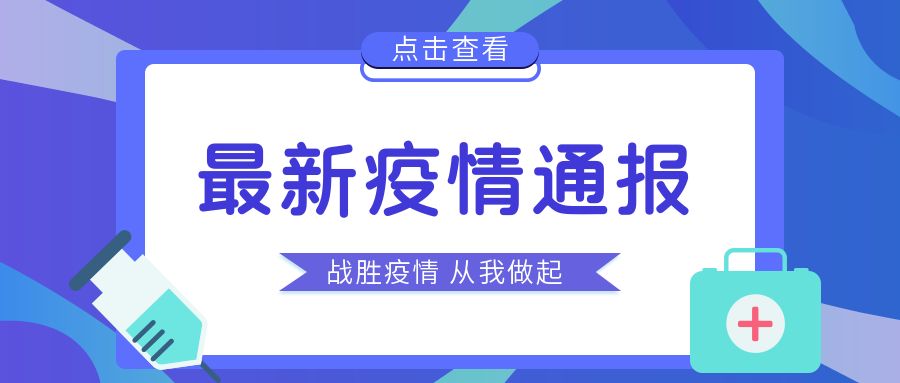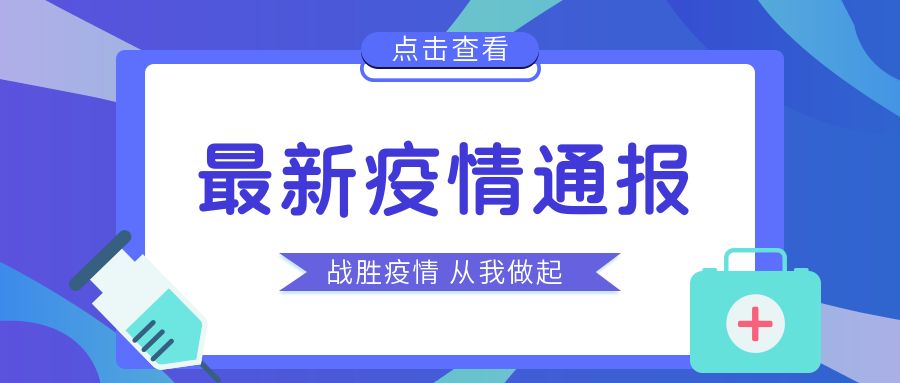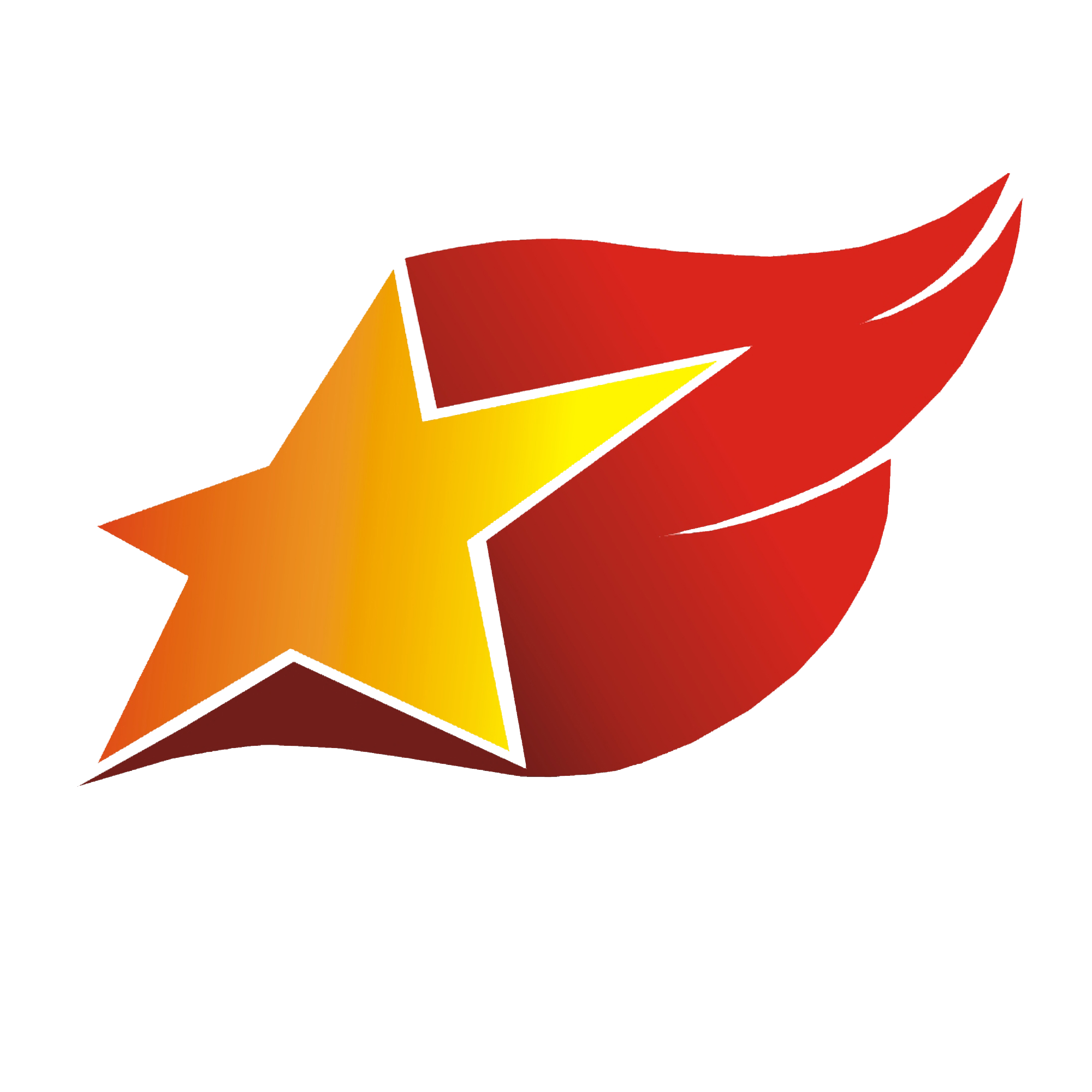4月5日,航拍三师托云牧场三连通往边境线的道路与山脉。 兵团日报记者 陈洋 摄

三师托云牧场三连党支部书记、连管会指导员王宇新骑马前往牧点(资料图片)。 王宇新 提供

4月5日,航拍三师托云牧场。 兵团日报记者 陈洋 摄

扫描二维码观看视频
●陆小龙 田磊
“再干6年,我就是这样打算的。”
王宇新的声音不大,但在下山疾驰的车里,每个人都听得很清楚。
认识王宇新,源于一次只差“一步之遥”的昆仑山之旅。本想着踏勘皑皑雪线,触摸巍巍界碑,然而,对我这样平凡的人来说,没有王宇新那般“托云”之志,很难见到心心念念的界碑。
一
4月4日,我们从喀什出发,沿国道一路向北。不远处的荒山把几户人家逼向路边,不大的地块绿油油的,地头开着几树粉色的杏花,细直的杨树环绕着它们,营造出一个微型绿洲。汽车在疾驰,这样南疆独有的春景一闪而过,给人一种“忽逢桃花林”的错觉。
车行不过60公里,道路两旁山峦对峙,越逼越近,直向我们压过来——这是进山了。大山的底色是荒凉的,忽然成排的徽派建筑从右侧闯入眼帘,让人不由惊呼。三师托云牧场到了。
托云牧场位于昆仑山北端天山南麓,西北与吉尔吉斯斯坦接壤,地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境内,始建于1951年,其前身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军后勤部的托云、木吉、英尔、阿英4个羊场和民族军十三师牧场合并而成,牧场流淌着部队的血液。
这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牧场,只有3个连队,总人口仅1100人出头。场部占地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社区、学校、医院、邮政所等有序排列。初到牧场,感觉这里的人们过着安宁的生活。
“牧场拥有多个兵团之最,比如海拔最高、生存条件最差、人口密度最稀。” 迎接我们的牧场副政委王庆芳说,“守边任务最重,这是我们的骄傲。”
我们要去的三连,离场部85公里。一路向北,雪山越来越近,海拔上升到3200米。
三连党支部书记、连管会指导员王宇新等候在路边。瘦削的身材,穿迷彩棉服,戴一副眼镜,黝黑的皮肤,声音听着年轻。“顺着这条路一直往上,就能走到雪线了。”他充当临时向导,带我们去看牧工平时上山巡逻的路线。
一路上,我跟王宇新攀谈起来。他告诉我,三连总人口130余人,除2名汉族“两委”成员,其余均为柯尔克孜族。有46名护边员,最小的23岁,最大的60岁,平均年龄37岁。巡边员中有夫妻档、兄弟档,他们半个月一轮换,常年戍守在边境线。
“牧工就是流动的哨兵,毡房就是流动的哨所。” 王宇新说,这一段边境线,依仗着三连的柯尔克孜族牧工几代人的接力戍守。连队是永不移动的界碑,一茬牧工老了,一茬牧工长大了,年老的牧工去世后,葬在向阳的山坡上,年轻牧工接过马鞭,继续为国戍守边关。
二
王宇新2015年从场部来到三连, 1991年出生的他,在这里陪伴牧工度过了6个年头。在我看来,这是很了不起的。
三连巡边海拔一路从3200米上升到4800米,年平均气温为0摄氏度,极寒天气为零下35摄氏度,放牧、放哨,几乎是生活的全部内容。“90后”的生活本该是现代的,多姿多彩的,然而,王宇新生活的底色是,工作服的迷彩色、昆仑山的土黄色和雪白色,这色调无疑是寂寞的。
“我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一种艰苦,可能是我注定属于这里。” 他的声音似乎是高原上的一声浅吟,能让人回味许久。
王宇新是土生土长的托云牧场人,父母那辈从陕西商洛来到牧场。“小时候吃惯了苦”,也是他觉得现在生活并不艰苦的原因之一。儿时家中的两间土块石头房依山沟而建,用水需要到两公里外的河边拉,无论冬夏,只不过冬天拉回来的是冰块。
“小时候是看着场部对面的山头长大,长大了在海拔高了1000米的地方看山。这里除了不能种树,别的都挺好的。” 2014年,从河南一所高校毕业的王宇新,没有丝毫犹豫,回到生他养他的牧场。“我的根在这里。”王宇新骨子里有很深的故土情结、反哺情结。
“6公里,在正常的行走状态下,一般耗时多久?”王宇新问我。
“一个成年人正常速度行走,大概需要1个小时左右吧。”
“山上下大雪,6公里,我们一般要用17个小时。”
冬季,山上的食物一个星期从连部往上运送一次,水和煤三天运送一次。遇到大雪天气,食物、水、煤的运送周期都是一个星期。煤,省着点用,水,只能靠融化积雪。这又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煤要节约,雪要融化。于是,山上的人忧心忡忡;山下的人心急如焚。
铲车开道,运送物资的卡车跟在后面。一个成年人站到雪地中,雪能到腋下,而1米厚的雪在冬天的高原更是常见。挪动,挪动,一米一米地挪动。山上的房子近在咫尺,但要接近它,却要以米计算、以分钟计算。
机械的马达声响彻雪山。17个小时,6公里,天不亮从连部出发,深夜才能到达。这就是冬天护边员真实的生存状态,这就是鲜为人知的边境线上的兵团人。
三
“护边员一个月的补贴是2600元,但他们的付出是无价的。”王宇新深知高原戍边之苦,所以他一心一意地想着连队的130余名牧工。
一年早春,一场忽然而至的大雪封闭了通往肖尔苏牧牧点的道路,积雪深度达到一米,道路不通,饲草料告急!羊群告急!牧点告急!
当时还是副指导员的王宇新正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窗外的积雪发愁,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思绪,看着来电显示的号码,他迅速接起电话:“牧点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
“草快吃完了,快救救我们的羊吧。”那头是牧工白先阿力焦急的喊声。牧点的多数牧工家出现了断饲草料的状况。
“我马上过去。”挂了电话,王宇新立刻跟场部汇报,借来两匹马,拉上卫生员英格拉就往牧点跑。虽说当时来三连已经两年了,可这是王宇新第一次骑马,他紧张地用腿死死夹着马鞍,不断催促马儿快跑。
“不要急,我们还有三四个小时的路要走呢。13年前,我给你爸爸带过路,也是走的这条路。” 英格拉看出了他的紧张,跟他聊起家常。
“谢谢你,英格拉。13年前你给我爸爸带路,现在又给我领路。”王宇新嘴里应着,心里想着受灾的牧工,心里还想着,这些牧工几代人坚守高原,陪伴过父亲现在又陪伴着自己,他们对牧场饱含深情,作为连队的当家人之一,一定不能让牧工吃亏。
从连部出发的时候,太阳还在头顶上,等到达牧点,明月高悬。王宇新顾不上暖一下失去知觉的手脚,颤颤巍巍地从口袋掏出了笔和本子,挨家挨户记录受灾情况。
第三天,救灾物资全部到位,他亲自上阵,直到最后一袋饲料送到牧工库房,才悄悄收拾了一下,换了身衣服,赶车去医院看望做手术的母亲。
到三连的第二年,也就是2016年6月,王宇新加入中国共产党,3年后他成了连队的“领头羊”。1500米海拔落差的进山路上落满了一个年轻人的成长足迹,连队130余名柯尔克孜族牧工见证了一名“90后”党员的为民初心。
四
入党那天的情景,王宇新清楚地记着。他握紧右拳,对着党旗宣誓,“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透过党旗,他仿佛看到了三连戍守的边境线。
护边员一年四季都在界碑前走来走去,无论风和日丽或风霜雪雨。王宇新多次参与巡边,他也跟老牧工一样,坚持走下去,一直走到界碑前,用双手擦掉界碑上的沙尘,扒开界碑周围的积雪,让界碑挺立在高山之上。
“那呼啸整晚的风,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王宇新告诉我,高原的风是肆无忌惮的,一旦风张狂起来,人无处躲藏。那天,风刮了整整12个小时,到了晚上,大有愈刮愈烈之势。风裹挟着雪,砸向护边员在山顶的住房。
住房是用彩钢板搭建而成的,在大风中“嘎吱”作响。到了深夜,房子实在承受不住风的百般折磨,“哐当——”,屋顶被掀开,瞬间不见踪影,风直往房子里灌。
山上待不住了,王宇新果断决定,立即撤往5公里外的牧点。在黑夜之中,在狂风的肆虐下,8个人相互扶持,喊着彼此的名字,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向山下撤退。
我不禁想象,在这样的冬夜,我这样的普通人会在有暖气的房屋里,或与家人在一起做饭说家常,或躺在沙发上惬意地翻看着手机。我们何曾想到,在边境线上,有一个年轻人,带着他的队伍,在跋涉,在抗争,在坚守。
“还有比这个更难的。”王宇新很平静地说,脸上甚至还带着一丝笑意。
这次,我们在山上看到了旱獭、黄羊,其实在冬天还有一种野生动物,那就是狼。冬天的高原万径人踪灭,飞禽走兽也消失了,狼自然会饿肚子。饿了,就会找到护边员住的地方。
那晚,云少,月亮正圆,把高原照得雪亮。忽然,房子后面巡边犬狂吠不已,但过了一阵,狗的叫声变了,变成“呜——呜——”声,“狗害怕了”,王宇新他们几个人因为没带武器,不敢贸然冲出。他们从窗户往外看,看到了6双让人不寒而栗的发光的眼睛。
狼群绕着房子转了很多圈,终于散去了。“所有人都深深吐出一口气。”王宇新说,“狼群围着房子绕圈子时,每个人都屏住呼吸,大气也不敢出。”
五
“为什么我觉得你是带着笑意在讲述狼的故事?”
“有句话不是叫笑对苦难吗?如果我哭丧着脸讲,那估计没人愿意来牧场了。”王宇新心里着实有些着急,他担心牧工队伍人员的流失,他担心年轻人不愿意来高原,他更担心戍边事业后继乏人。
有一年,连队来了个年轻的姑娘,那会儿还是团场实行综合配套改革前,年轻人是牧场分来的“连官”。王宇新满心欢喜地给姑娘扫了屋、生了火、铺了床。他感觉到姑娘对这里十分不适应,他想用这些贴心的方法为连队留住年轻人。
可是,第二天一大早,姑娘还是哭着离开了,走之前她说:“对不起,这个地方我实在待不下去。”
王宇新不怪她。“我们这里实在是太艰苦了,连队牧工的孩子都没几个愿意回来。”连队里哪家的孩子在外读书,王宇新一清二楚,趁着孩子们暑假回连队,他都会去摸底了解情况,问他们有没有回乡的打算。
“绝大多数孩子没有这样的打算。”王宇新长长叹了一口气说,“我很担心,真的很担心。”作为一个偏远连队的“两委”,他不无忧虑。好在,现在兵团各级都十分重视这项工作,都在为加固连队这个“基石”出谋划策。
王宇新心里有很多话要对年轻人说,“在山下在城市,人容易浮躁和迷茫;在高原,年轻人会变得平静,然后能找到人生的方向。”他还说,以后,他想让孩子跟自己一样,留在牧场。
说起孩子,话题轻松许多。王宇新的妻子叫衡田田,是三师伽师总场人,目前在托云牧场场部上班,二人育有一子,父母身体健康,在跟前帮衬,日子过得幸福。“不能说美满,也有缺憾,比如20天甚至更久才能回家一趟。”王宇新说,好在家里人都支持他,让他少了不少后顾之忧。
我对王宇新说:“你这么年轻,能在高原待6年,这本身就很了不起。”
他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就是我的人生啊。”
是啊,每个人都有他的人生轨迹。王宇新的轨迹或许就是从海拔2200米的场部,到海拔3200米的三连连部,再到海拔4800米的边境一线。如此循环往复。有一天,他也会老去,高原的风会在他脸上刻满印记,但他心中将永驻“托云”之志——托起边关的云,守卫祖国的边。
来源:兵团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