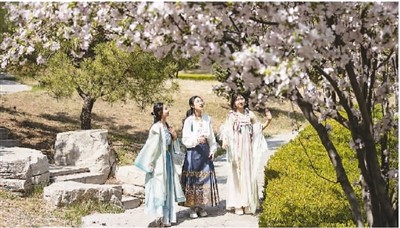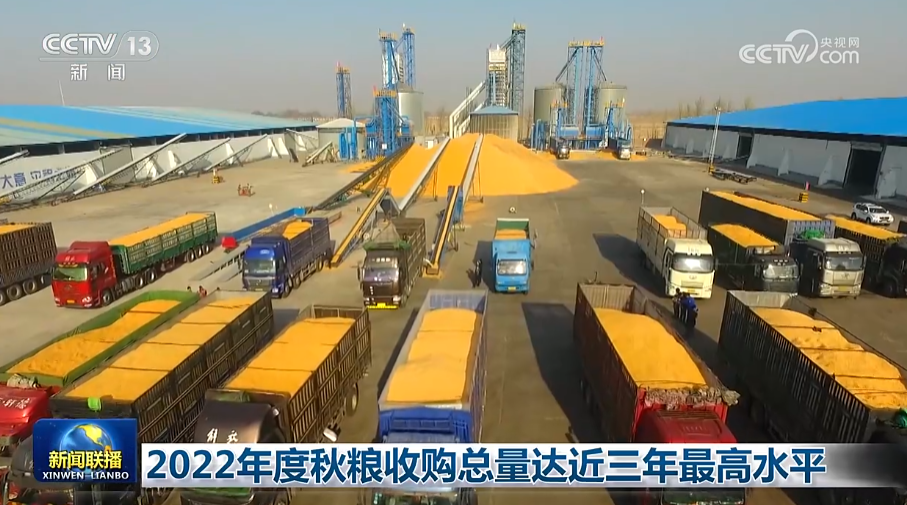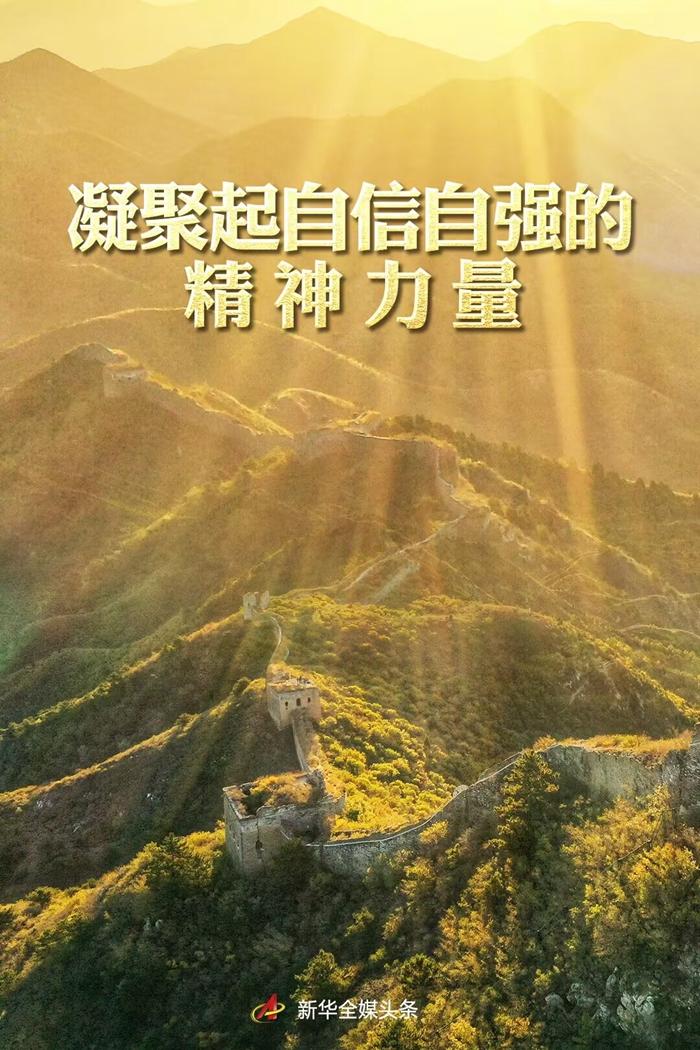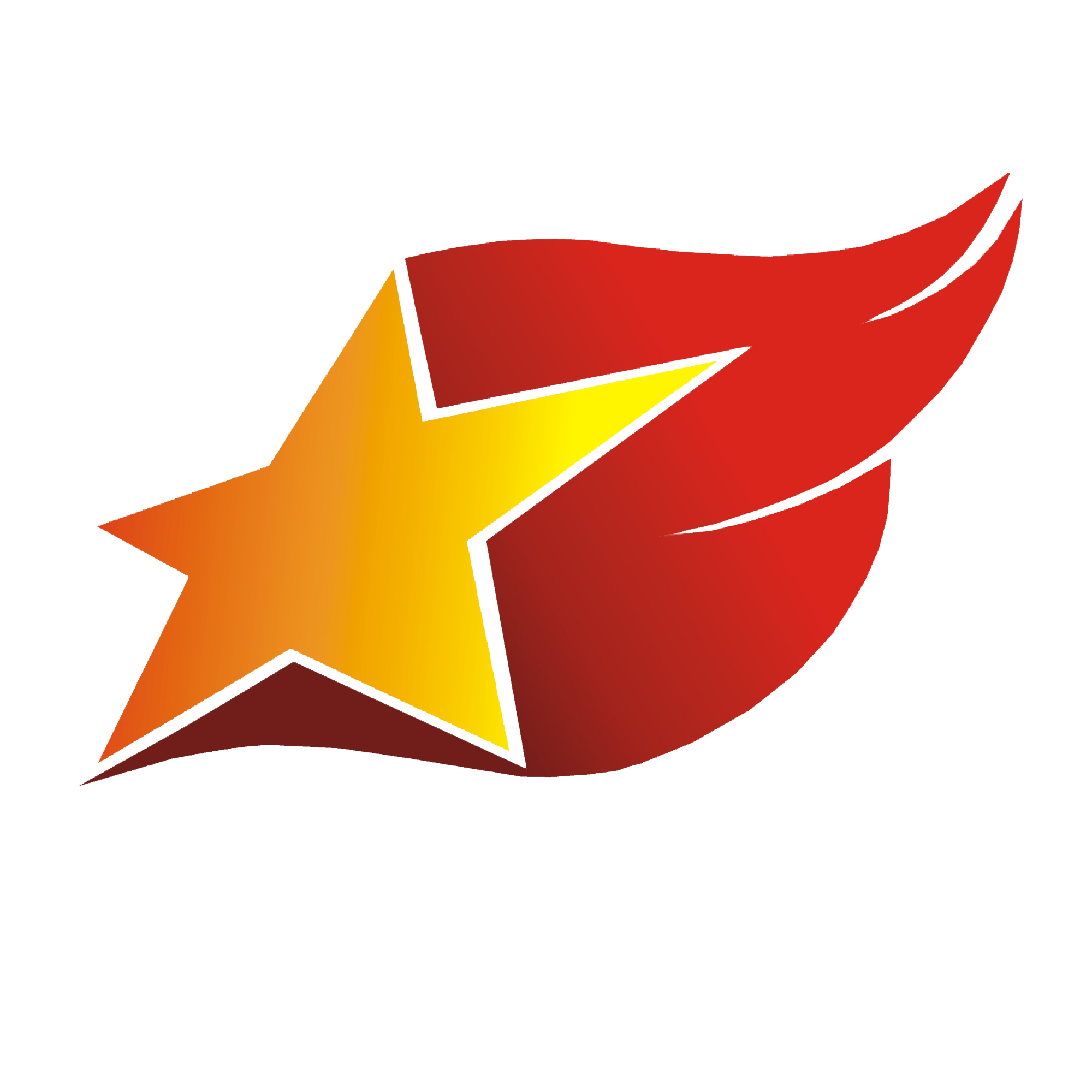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的壁画。□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打开祖国的地图,我们会发现在西北边陲的新疆天山南麓有一条长长的河流——塔里木河,自西向东蜿蜒穿行于塔克拉玛干沙漠,消失于东部的罗布泊区域。而在它的上游则有一支隐秘于沙漠中自南而北流淌的河流,就是克里雅河。在此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实证了中原文化对这一区域的深刻影响,也生动展现了各民族文化在这里的交往交流交融。
从飞机上俯瞰克里雅河,河流从昆仑山主峰乌斯腾格山奔腾而下,绕过于田县北部,自南向北逐渐消失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依宽阔的古河床,结合史料可以推测:数千年前,克里雅河水曾汇入塔里木河,形成了纵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绿色走廊,搭起塔里木盆地南北两道交通的桥梁。巍峨的昆仑山高峰终年积雪,遍布的深谷溪水涓流,汇成若干河流奔腾而下,涌入沙漠腹地,所经之处形成河湖相冲积平原。生活在这里的先民就沿河流沟谷而居,繁衍生息。而随着当地气候逐渐干旱,昆仑山冰川雪水补给不断减少,流域水量也随之减小,无法到达沙漠深处,致使克里雅河尾闾不断往南退缩,绿洲长廊也不断退缩,如今已经退缩至达里雅布依乡附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考古学者对克里雅河流域进行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1993年,“中法克里雅河联合考古”项目实施,发掘、探索克里雅河流域古代文化遗存面貌。这项持续20余年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截至目前,在克里雅河流域已发现100余处古代文化遗存。这些遗存顺着河流,从下游向上游,年代逐渐变晚。
下了飞机,我们驱车直达克里雅河下游,遵循着这个有趣的规律逆流而访。首先来到克里雅河尾闾的青铜时代遗存,这里以北方墓地及其遗址为代表,文化面貌与罗布泊地区的小河墓地非常相似。
北方墓地于2008年被发现,当时,已遭盗掘破坏的墓葬至少有60座。借助无人机观察,可以清晰地看出墓地整体呈椭圆形,南北长48.5米、东西宽34米,高约4米。在墓地中部偏南处残留有一排木栅墙,栅墙的木柱直径10余厘米。考古人员在木栅栏南约2米处发现露出地表的男根立木,推测可能还有未被破坏的墓葬。此外,该墓地大量出土了黍,表明中原文化早在青铜时代就已对新疆地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墓地东北14公里处保留有一排房址,清晰可辨的仅有3间,大致呈东西向排列。西侧两间保存较差,仅存房屋墙基部分;东侧房屋则还保留有一间屋顶。房屋的建造方法是先用胡杨木柱并排栽立,然后用芦苇在外侧横向绑缚一层,最后敷一层泥巴,形成与南方极为相似的“木骨泥墙”墙体结构,透露出中原地区建筑风格在这一时期对塔里木盆地的影响。
屋内有几根顶端带叉的立柱承接横梁。房屋的门开在南墙中部,因为那里有几根长方形木板和一根顶部有榫头的木柱。而屋顶则在并排平铺的一层木头上铺一层芦苇,再在芦苇上覆盖一层羊粪。在房屋四周,我们可以看到大量遗存:刻划纹或压印纹的陶片、铜箭镞、石祖、石锥、石镞,以及玉斧和细石叶等玉石器。
一览早期的遗迹以后,我们向南,就来到汉晋时期的遗存。它们以圆沙古城和喀拉墩古城为代表,主要包括城堡、民居、佛寺、灌溉渠道等。
圆沙古城是一处汉代古城。它最早于1962年被原兵团农一师勘察设计院发现,当时被称为“新聚落”;后又于1994年被中法克里雅河联合考古队发现,根据当地对其“尤木拉克库木”(意为“圆沙”)的称呼,命名为圆沙古城。古城平面为不规则圆形,墙体大多不直,因水或风蚀,城垣破坏严重。
据初步测量,古城周长995米,南北最长处330米,东西最宽处270米。残存的城垣总长度为473米,顶宽3到4米,高3到4米,最高处达11米。城垣以两排竖直的胡杨棍棒固定纵向红柳枝为墙体骨架,外侧用泥土块垒砌,再用胡杨枝、芦苇夹淤泥、畜粪堆积成护坡。其与早期的墙体建造方法既存在继承,也存在发展。继承是利用当地的胡杨木排插墙体骨架,发展则是在外侧采用泥土块垒砌,而非泥巴抹平。
走近南墙中部和东墙北段,会发现各有一座城门,很显然,南门规模较大,保存也较完好,城门两侧的两排立柱形成门道。放眼城内,已基本被流沙覆盖,仅见6处建筑遗迹,地表散布残陶器、石器、铜铁小饰件及料珠等遗物,以及少量的动物骨骼。此外,在城内还能看到存储麦、粟等谷物的袋状灰坑或窖穴,还有马鞍形石磨盘,这些工具用来加工谷物。在城外能够看到发达的灌溉系统,沟渠纵横成网,排列有序,这表明了圆沙居民在城外从事农业生产。黍粟的大面积种植,更能说明在汉代粟的种植和加工技术在克里雅河流域已大面积推广。
在距古城不远的地方,我们看到了一些墓葬。从距离来判断,这些墓葬应该属于生活于城中的圆沙先民。他们的墓葬特征明显,地表有封堆标志,墓室除了竖穴土坑墓外,还有带二层台的竖穴土坑墓、竖穴棚架墓,带斜坡墓道的竖穴棚架墓等类型。葬具种类较多,有木棺、树棺、尸床等。墓葬出土文物丰富,既有来自中原的漆器、织锦等,也有来自西方的玻璃珠。证实了当时圆沙古城正处于中原文化向西传播和吸收西方文化因子的发展之路上。
告别圆沙古城,我们转到晋代的喀拉墩古城。
这一时期的古城布局合理,结构完整,包含了中心城堡、民居、寺庙、灌溉渠道等遗迹。城堡平面呈正方形,本体采用泥土、树枝混筑而成的“木骨泥墙”建造形式。从中也能看到中原建筑风格影响下的建筑构件和房屋特征。
城堡内有多处木构建筑,其中发掘出两组民居。一组位于城堡南侧,另一组位于城堡的东北,均因流沙的淹埋仅暴露出一些圆木立柱,总面积约200平方米。
房屋内还保存了当时居民使用的一些陶器、木器等生活用具,以及残留的谷物、葡萄籽等。城堡南北两侧也布满灌溉渠道,干渠与支渠交错相通,透露出灌溉农业的发达。
晋代的和田地区是丝路南道上的佛教中心,喀拉墩遗址很可能是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中国佛教遗存之一,是弥足珍贵的佛教文化遗产。在喀拉墩古城南侧有“回”字形佛寺遗址,其建筑结构亦采用当地的建造方法——“木骨泥墙”,与邻近的尼雅及楼兰遗址一致,但墙体很厚。
佛寺布局,中心为正方形建筑,推测是中心塔;边长2米,只残存底部,黏土质。在中心塔外壁及回廊墙壁内外侧绘有壁画,使用的颜料主要有红、橘红和黑三种。从残存的壁画初步看出,绘制的是佛陀肖像,与和田地区及其西的一些遗址具有相似之处。从壁画和塑像的风格看,喀拉墩佛教遗存表现出中亚、印度与中国佛教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
离开汉晋时期的印记,我们来到了唐代的“象牙房”,即丹丹乌里克。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其为唐代丝路南道上的重镇“杰谢镇”故址。作为安西四镇中于阗军镇防御体系中的一环,它是扼守丝路南道的一处战略要地;同时,作为丝路沿线的商贸之地,过往商人也多在此居留,与当地居民、唐朝军人及其家属杂居共处,使此地逐渐成为多民族多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所。
一眼望去,遗存规模大得令人瞠目。遗迹主要分布在南北长约4.4千米、东西宽约3.3千米的范围内,现存各类遗迹70余处,包括城墙遗址、官府衙署、寺院佛堂、居民住宅、果园、冶炼遗址、窑址等。其中佛寺遗址达15处,占建筑遗址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居住遗址功能也很明确,主要有大厅、卧室、储藏室、厨房、畜栏、果园等。建筑方法仍然是采取塔里木盆地南缘广为流行的“木骨泥墙”式。
“一条千年古河道,浓缩半部人居史”。克里雅河流域先民对黍粟种植和加工技术的继承和向西传播,从青铜时代直到汉晋时期沿用“木骨泥墙”,对中国化佛教“回”字形寺院的使用等,都体现了中原文化对古代克里雅河流域深刻而持续的影响。对西来佛教的本地化、玻璃珠贸易,以及多种文字的使用,反映了克里雅河流域先民对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形成作出的贡献。(郭艳荣)
编辑:张刘洁 审核:赵华
来源:新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