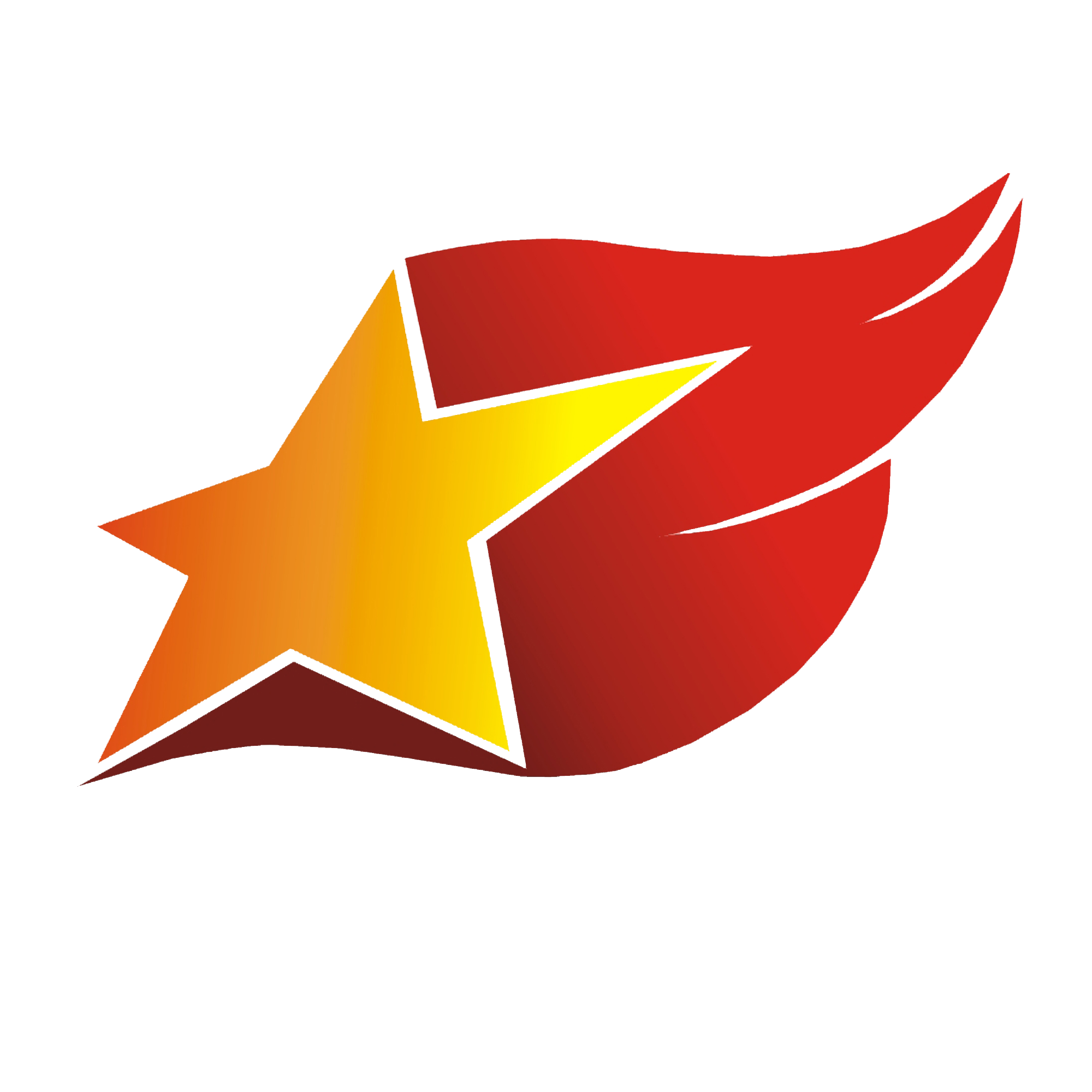“过年了,过年了,穿新衣,戴新帽”。虽然距离春节还有半个多月,但是大街上就已贴满“拜大年”的广告,超市里购买年货的人也明显多起来。无论男女老少,人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气洋洋的味道,一边挑选着琳琅满目的商品, 一边思考着如何度过这个美好的新年。眼前的一切,令我的心暖洋洋,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向了那个遥远的年代,那个记忆里的童年。

生于70年代的我,童年记忆里最渴望的就是过年。因为只有过年才可以吃上平时很难吃上的饺子,才可以穿上平时很难穿上的新衣服,才可以得到平日里难以得到的“零花钱”,才可以……总之,这许多的“可以”为我带来太多的童年乐趣。也只有在过年的时候,父母对我们的要求也没有那么严格了,白天不用写好几个小时的作业,晚上看电视想看到几点就看到几点。父亲的斥责、母亲的唠叨不再存在,与我们的对话中也多了几份温情的味道。
记忆里过年最忙碌的,还要属母亲与大姐。父亲是一名水利工程师,常年工作在野外,母亲与比大我十几岁的大姐便承担了家务重任。离过年还有半个月,她俩就去市场采购,回家后母亲负责卤肉、蒸馒头、炸带鱼,大姐则负责用烤箱做点心。我与二姐那时还小,好多事情还不太会做,就围在母亲和大姐身边,做些零零碎碎的工作,比如帮母亲一起包包子,给馒头和包子点红点,还与大姐一起做杏皮、炸麻花、烤巴哈里。记忆里那时候要做的食物可多了,包子都要包好几种馅的,有白菜粉条肉的,有皮牙子羊肉馅的。家里的蒸锅几天里都在冒着袅袅的热气,一笼笼蒸好凉透后,被放进大纸箱里。然后又开始团肉丸子,这也是过年才能吃上的美味,团的时候心中总会有美美的期待,以及浓浓的喜悦。丸子一个个团好后,母亲娴熟地将它们投入油锅炸熟,凉透后,再一个个放进纸箱里。那时候过年,家里总要备好多纸箱,有时候纸箱不够用了,我们就将报纸铺在塑料大盆里,把食物摆在上面。过年家里来客人时,取出放在蒸锅里热一热就可以端上来吃了,十分方便。所以,童年里年的味道,总是与肉丸子、肉包子、巴哈里的香气联系在一起。这是年的味道,也是爱的味道,属于家的味道。

这一切准备好了,春节的脚步也就临近了。大年三十这一天,父母一大早就起来,开始为晚上的盛宴做准备。父亲也是从这一天开始才正式休息。他是个勤快闲不住的人,一大早就忙着做饺子馅儿,肉馅有两种,一种是白菜肉馅的、一种是萝卜肉馅的。父亲做饺子馅的样子我至今还记得。他坐在卧室黑色的单人沙发上,左手扶着椅子,右手持长筷,认真地搅拌盆里的肉馅,神情喜悦,与素日里威严的模样大有不同。
整整一天,家里都弥漫着肉与蔬菜混合的香气,还有一种潜藏于内心深处,一不小心就流露出的欢乐,这种欢乐是多么珍贵啊!它是春节这个隆重的节日赋予我们的,一切都笼罩着一种脉脉的温情。
父亲、母亲还有大姐忙碌着厨房的活计时,我与二姐就开始打扫房屋,还要将前几天清洗过的窗帘挂好,将新床单、新被单铺在床上。而那些院子里的活儿自然就是交给男孩子干啦!一个上午,哥哥在大门口攀高爬低,贴春联、粘窗花。春联、窗花红彤彤,一扫冬日小院平日里的朴素、清冷,看着就喜气。在这种喜气洋洋的氛围里,迎来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其中,当然也有我家的。鞭炮的声响一停,母亲巧手烹制的年夜饭就端到了饭桌上,一家热热闹闹围在桌前,开始享受忙碌后的安逸。

吃完饭后全家人围在一起欣赏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陈佩斯、朱时茂的小品逗得我们大笑不止,可遗憾的是,我从来没有等到“难忘今宵”那一刻,往往是联欢会看了不到一半,就被小朋友们叫出去放花炮,二踢脚、窜天猴、夜明珠、仙女棒……花炮的种类很多,玩到高兴处,还会趁大人们不注意,爬到房顶上燃放烟花。当绚丽夺目的烟火绽放在微微发红的天空,一种极致的快乐也在心底绽放。哦!过年了,也只有过年我们才能享受到这种无忧无虑的快乐,这种快乐一直持续到大人们呼儿唤女的声音响起。看看墙上的挂钟,时间已近零点,又到了吃水饺的时光。每家每户的水饺里总有几个包着硬币,据说谁能吃到谁在这一年有福。
不知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许多事情都已看淡,但对于过年的期盼与喜悦却从没有变过。每当到了过年,我总是会欢欢喜喜地与家人一起上街大采购,一起大扫除,一起为孩子购买鞭炮,还会去银行兑换成沓的崭新压岁钱,放进红包里压在枕头下,在新年第一天为他们发放。看见孩子们欢喜的笑脸,我也会不由自主地欢喜起来,忍不住回味起童年时浓浓的年味。那年味存留于闪烁的烟火中,存留于喷香的饺子里,更存留于对逝去亲人的追念中。
时光荏苒,岁月流转,我们年复一年过着平凡的日子,而年味的存在、存留,把寡淡的日子涂成华彩,如此,便是金色年华。
(作者 李晓寅:新疆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于自治区伊犁河流域水利管理中心,现居新疆伊宁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