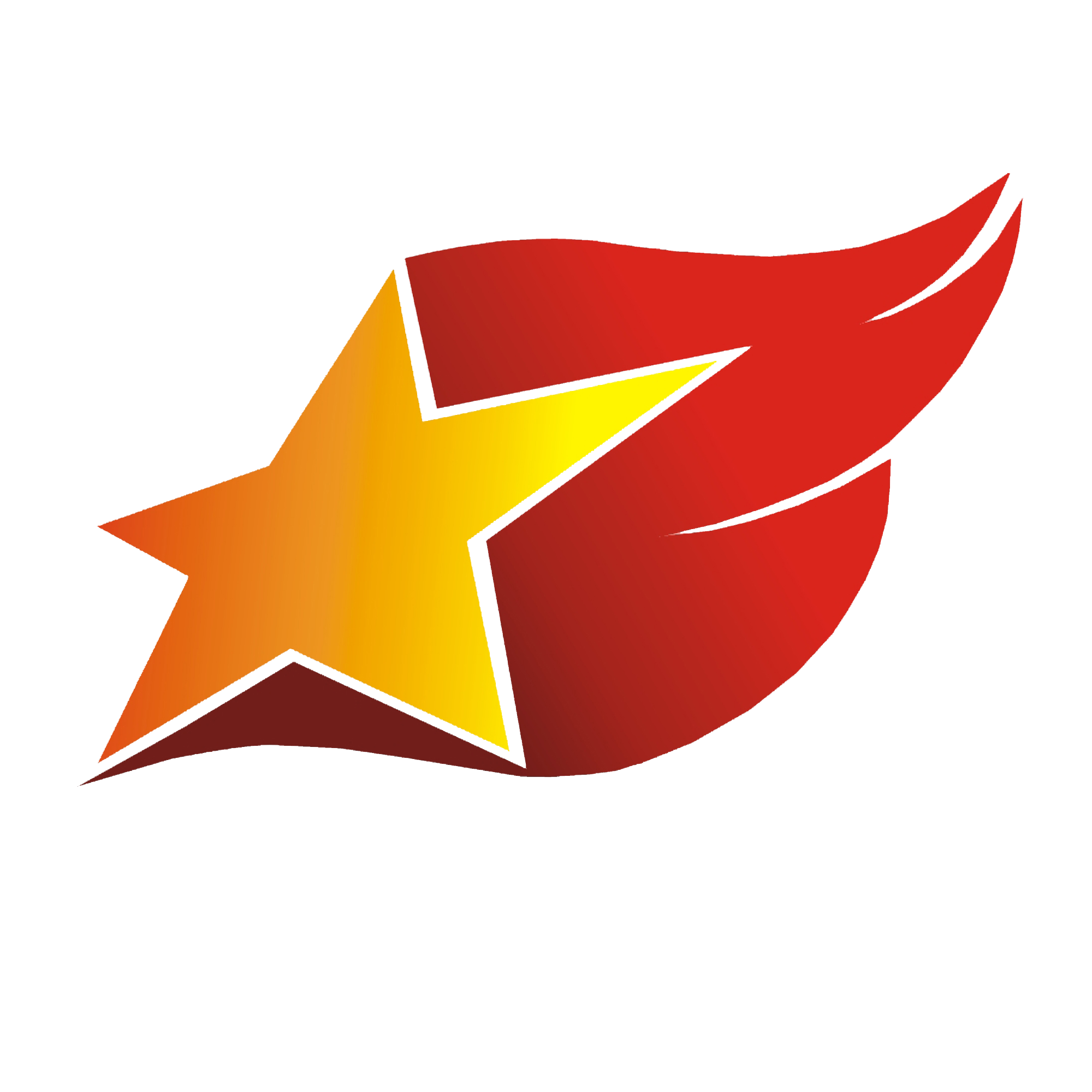爷爷的木箱子底下压着张皱巴巴的酒标,那是20世纪70年代第一批伊力特酒的包装纸。泛黄的纸面印着天山雪峰,边缘被摩挲得发毛。他总说,第一次喝到伊力特酒那年,农场小麦丰收,场部食堂炖了整只羊,酒倒进粗瓷碗里,满院子都是粮食发酵的香气。
那时候父亲刚进酒厂当学徒。车间里蒸汽腾腾,搅拌机嗡嗡作响,他跟着老师傅学看酒花、测度数。冬天车间没暖气,父亲的手背长满冻疮,却总把新酿的酒样揣在怀里保温。爷爷常去车间看他,用搪瓷缸装些下酒菜,父子俩蹲在锅炉房旁喝酒。酒从喉咙烧到胃里,说话的声音都带着热气。
我出生那年,父亲从酒厂带回特制的纪念酒。酒坛用红绸缠着,摆在堂屋条案上。爷爷戴着老花镜,用毛笔在酒坛侧面写下我的生辰八字。每年除夕夜,他都要拧开酒坛闻一闻,说等我考上大学,就用这酒办升学宴。
小学时,我常跟着父亲去酒厂。车间里的陶缸比我还高,空气中飘着酸甜的发酵味。父亲教我辨别不同窖池的香气,说老酒窖里住着“酒神”。有次我偷偷尝了口新酿的酒,辣得直掉眼泪,父亲笑着用衣角给我擦脸,顺手往我嘴里塞块冰糖。
爷爷退休后,在院子里搭了个葡萄架。夏天傍晚,他坐在竹椅上,面前摆着伊力特小瓶装酒和一碟花生米。我做完作业,就搬个板凳坐在他旁边。他会给我讲年轻时支边的故事,讲到激动处,就仰头喝口酒,喉结上下滚动。酒气混着葡萄藤的清香,成了我童年最深的记忆。
父亲后来当上了质检员。每次新产品上市,他都要带回家几瓶样品。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父亲给每个人倒一小杯,让我们说说口感。爷爷总说还是老味道好,我学着大人的样子咂咂嘴,说有股粮食香。母亲在一旁笑,说我们爷孙俩喝空气都能品出花来。
高考前三个月,爷爷查出患重病。他躺在病床上,还惦记着那坛存了十几年的酒。父亲把酒坛搬到医院,拧开盖子让爷爷闻。老人浑浊的眼睛突然亮起来,用虚弱的声音说:“等娃考上大学,你们替我喝……”
那年秋天,我捧着录取通知书站在爷爷坟前。父亲打开那坛酒,分别倒进三个杯子。酒液金黄透亮,在阳光下微微晃动。我们爷俩对着墓碑把酒洒在地上,剩下的分着喝完。酒顺着喉咙滑下去,又辣又暖,像爷爷生前拍我肩膀的力道。
工作后我留在外地,每次回家都要带几瓶伊力特酒。母亲把空酒瓶洗净,插上当季的野花摆在窗台。父亲的白发越来越多,喝酒时不再像年轻时豪迈,总是慢慢抿着。他说现在酒量不行了,但闻到这酒香,就想起在酒厂当学徒的日子,想起爷爷蹲在锅炉房旁喝酒的模样。
去年春节,我带着妻子、孩子回老家。饭桌上摆着三瓶伊力特,分别是爷爷年轻时的老包装、父亲工作时的经典款,还有我特意买的纪念版。儿子好奇地盯着酒瓶,问能不能尝一口。我笑着给他倒了小半杯饮料,说等你长大考上大学,爸爸就用这酒给你庆祝。
夜深了,孩子睡下后,我和父亲坐在葡萄架下。月光洒在酒瓶上,折射出细碎的光斑。父亲说起他第一次跟着爷爷喝酒的情景,我说起小时候在酒厂偷尝新酒的糗事。酒一杯杯下肚,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故事,都随着酒香漫了出来。
院子里的葡萄藤又抽了新芽,缠绕在爷爷当年搭的架子上。酒瓶里的酒液随着说话的节奏轻轻摇晃,倒映着三代人的影子。从爷爷的搪瓷缸,到父亲的玻璃杯,再到我现在用的陶瓷盏,伊力特的味道始终没变,就像我们家的故事,在酒的醇香里一代代传下去。(作者:王旭 现居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